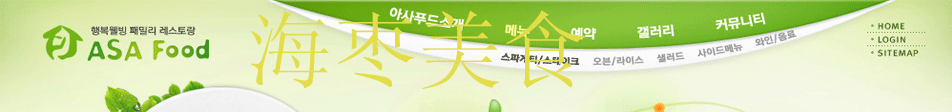|
禅茶一味说南岳(下) 到了元代,除了开头讲到的常州吴克恭,无锡倪瓒、常州谢应芳等茶客,也因避乱寓居南岳寺。此时,南岳的僧、寺还在,可惜茶园的光景已大不如从前。倪瓒云:“罨画溪头唤渡,铜官山下寻僧。”云林居士来此,寻僧是一,而问茶,又是其一。所以又说:“木鱼晨粥同僧赴,仙掌春茶破闷煎。”稍后来到此地的谢应芳,运气就没有这么好,他在诗中写道:“南山茶树化劫灰,白蛇无复衔子来。”“谁能遗我小团月,烟火肺腑令一洗。”龟巢老人一生颠簸,念念不忘的是南岳蛇茶。可惜铁蹄战火之下,百姓离散,而那记忆中的满山苍翠,竟然也化作了一片“劫灰”。世道轮回中,凡人圣人难逃厄运,灵草凡芽同样也在劫难逃。好在天地有好生之德,何况是瑞草之魁的茗茶!时过境迁,南岳的故事在继续,蛇茶的名声又鹊起。明初,被朱元璋选定为十大高僧之一的夷简禅师住持南岳寺,经过他的努力,南岳寺、南岳茶又一次得到了重生。当时,本土诗人马治有诗云:“灵芹发天秀,泉味带香清。蛇衔颇怪事,凤团虚得名。采摘盈翠笼,封贡上瑶京。愿因锡贡余,持赠君远行。”南岳茶再次走进宫廷,而文人墨客到此,有幸能尝到“贡余茶”的味道,已经非常难得了。至嘉靖时,宜兴县令方逢时说:“阳羡山川重今古,紫笋香茸世稀有。白龙衔种来仙宫,天风散落铜官首。”年轻的方县令也许觉得“白蛇”还不够神威,直接改作“白龙”,真不愧是“春秋”场中好手。特别是在他一手推动下,宜兴有了“阳羡十景”一说,铜官山的“铜峰叠翠”“阳羡茶泉”双双入围,诗词歌咏、丹青绘画,难以胜计。著名诗人、宜兴才子邵半江(珪)在《春山省茶》诗中说:“南岳山前春欲动,肩舆轻载路非赊。”“滥觞正苦权门牒,传语卢仝莫浪夸。”南岳山的贡茶,再一次成为宜兴百姓、南岳山僧的额外负担,欲诉无门。而徐懋曙诗中不无调侃地说:“贡题上品珍天府,锡卓芳流争戒台。自是荐新勤长吏,几人不道采茶回。”一片小小的树叶,让四月的宜兴人忙忙碌碌,除了百姓、山僧,又加上了当地的“长”和“吏”。宜兴县乃至常州府里,为这粒粒茶芽丢官罢职的,大有人在。阳羡茶的扬名历程中,又融入了百姓不知、官员难言的一种怪味。明万历中,吴江诗人俞安期因爱阳羡茶而隐居南岳山,改字“羡长”,自称为“阳羡山人”。俞山人在南岳之巅,筑茅庵而居,并在门前屋后艺茶种树,简单度日。晚年,因久无子嗣,便在鹫峰寺设百日无遮大会,应祷而生了两个儿子。其长子长大之后,勤奋好学,但心向佛门,最终成为临济宗一代宗师,此人就是箬庵通问。俞山人有许多诗文记录此事,其中有云:“茶苑蛇衔种,神祠犬作牲。”“艺茶初赤壤,种树已青村。”禅、茶之味,在俞大山人、箬庵通问两代人身上,结下的称得上是一种前世因缘。俞山人的举动也圈得了不少“粉丝”,明末清初,许多流浪者、避世者在南岳山结茅而居,植茶莳蔬,苦行求渡。据南岳寺的资料显示,南岳山四周有“七十二茆棚”之说。清代初年,宜兴城里的吴洪裕首先移居山下的兰墅,植兰艺茶,鉴古玩画,最后,在绝望中将毕生所藏付之一炬,其中就有黄公望的名作《富春山居图》。幸亏其侄及时赶到,这传世名画才逃过一劫。吴家所余茶园田产,全部奉献于南岳,改成了枫隐禅院。无锡诗人徐孝均也是隐居者之一,因其名声在外,南岳寺僧留其居于本寺的反哺庵。徐孝均则在庵侧筑了“半亩居”,常与阳羡词人陈维崧、徐喈凤、曹亮武、万树等宴坐品茗,谈诗论经。徐诗人也修行成了词僧弘伦,也就是迦陵诗词中常常提及的叙彝上人。弘伦有诗云:“公忙自拨松根火,阳羡茶斟宣庙磁。”《满江红·移锡金鹅山》中说:“洗钵池头鸥似雪,焙茶炉外山如沐。”而宜兴诸诗友也皆有唱和之作。期间,陈维崧有首诗云:“吾邑介宣歙,边幅实狭窘。墟烟杂旊甀,津筏编茶笋。”“昨年解战船,拽绝千牛靷。”“前年送军粮,十室九室尽。”“明知骨髓干,苦说租庸紧。”宜兴物产丰富,有鱼有米,有茶有陶,但天灾人祸之间,又加上了苛捐杂税,百姓无从安生。凡人生命,就如开水之中沉浮的小小茶芽,绝望之中,牺牲了自己,但泡出的不可能是一壶香茗。清代中期,也有过一段承平时间,南岳茶的滋味也再一次鲜香起来。吴锡麟的《阳羡采茶曲》中说:“一雨转春和,东风发瑞草。借问唐贡佳,何如南岳好。”南岳蛇茶,又成为阳羡之最,为时人所趋奉追捧。好景不长,道光之中,沿海被难,甬东难民涌入宜兴山中,茶园茗柯,被山芋时蔬挤占。至咸丰时,江南遭太平军之乱,寺庙被毁,寺田庙产,侵占殆尽。僧走寺毁,茶枯灰冷,重新热闹了数百年的南岳禅、蛇种茶,俱归寂静。光绪年间,在惟一禅师、仁智法师等人的操持下,南岳山门艰难地重新树立了起来。宣统时,宜兴周志伊在《阳羡茶考》中记述说:“阳羡之茶交推南岳,一时争致,官府征需无艺,寺僧苦之。”南岳寺的钟鼓,日复一日,劝不醒“不识茶人苦”的迷途者;南岳寺的芳草,如脂如膏,反倒引来了“争言茶之味”的嗜利客。到了改朝换代时刻,南岳茶再一次沦落到只有人来“搜刮”、没有人来“繁植”的尴尬局面。当然,这种状况并未在民国年间绝迹,南岳寺周围的茶园,终于在时局动荡中湮没将尽。同样,南岳寺的境遇也日益低落,僧人众散,门庭破败。解放之后,在当地群众的努力下,南岳四周的茶园、茶事渐渐恢复了起来。而南岳寺的晨钟暮鼓,迎着朝霞,伴着明月,时时刻刻悠扬飘荡,似乎总在提醒着什么。自古以来,苦荼枯禅,喫茶参禅,是一是二,无从言说。而阳羡茶与南岳寺的关系,也非三言两语可以厘清。这里的佛门子弟本来是自植自采、解渴待客之举,不经意之间,加入到修贡进奉、争宠邀功之列,朝代更迭,战火兵燹,又无奈地经历了寺废茶荒、僧走茶尽的伤痛。此寺此茶,本来是一,万物平等,宿命使然。至于南岳禅茶传统,本来是超凡的仙事、脱俗的雅事,而后又成为皇家的“圣事”、宫廷的“秘事”,最终演变成僧人的怨事、百姓的痛事。颗颗茶芽命运,如同众生性命,沉浮展卷,置身于铜釜瓦罐,融化在清泉浊水,全是造化。一杯茶汤之味,也是一席禅言之味,此中不是什么空味玄味,有的也只是人间千姿百态的烟火味。续完》》》 长按
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