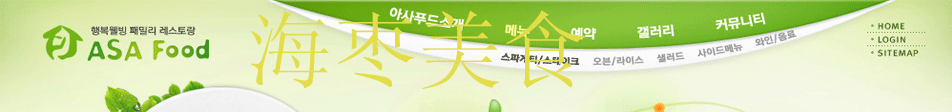|
一、仙人就是山中修炼的人 提起道教的仙境,从古自今,都是令人心仪和神往的。李白诗云:“问余何事栖碧山,笑而不答心自闲,桃花流水沓然去,别有天地非人间。”诗中描写的就是美丽的、令人神往的仙人境界。 李白早年向往神仙,曾经在峨眉山、青城山求仙学道。据王伯详的《增订李太白年谱》记载,他曾经在齐州紫极宫接受了道教的道箓,也就是成为了道教的弟子。据说李白还炼过金丹,是否还炼过内丹术就不得而知了。不过,从他这首诗却可以看出,李白自得仙人境界的深意,难怪世人称他为“谪仙”。 在中国文化的孕育中,这种仙人世界究竟是个什么模样呢?这样话题非常的有趣,不过,要说清楚这样的话题,我们依据的材料却十分有限,因为谁也没有到过仙境,好在中国的文学作品中不乏仙境之描写,我们可以对照看看,也许能够勾勒出一幅简单的图画来。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,由于统治者的高压和战乱频繁,人民少有安居乐业的时候,一遇乱世,更是“赤地千里,饿殍载道”。面对痛苦的现实,古代的士人无力改变社会,但他们却在文学的想象中描写了理想的社会。晋代文学家陶渊明在《桃花源记》中就虚构了一个类似的仙境: “晋太原中,武陵人捕鱼为生。缘溪行,忘路之远近。忽逢桃花林,夹岸数百步,中无杂树,芳草鲜美,落英缤纷。渔人甚异之,复前行,欲穷其林。……其中往来种作,男女衣著,悉如外人。黄发垂髻,并怡然自乐……” 作为现实的对照,陶洲明笔下的桃花源是充满诗意的田园,显然也是他心目中理想的小农经济社会。有趣的是,武陵渔人回来时尽管处处作了标记,可是,太守和南阳高士刘子骥沿着标志寻访桃花源时,却再也找不到去路了。原因何在呢? 其实诗人想象的就是不同于现实的时空,它只是存在于人的想象中,如果世俗之人能够随便涌入这个理想的社会,那也就不是仙境了。陶渊明晚年居住九江,曾与庐山的僧人慧远时有往来,因此很可能佛教的净土思想对他的文学想象有所影响。 桃花源尽管很美,但以道教的观念来看,只能算是隔世,离仙境还是有区别的。那么以道教的观念看,什么样才是仙境呢?我们先看看仙字的字义。仙字的本义就山中人,仙人就是山中修行的人,由此推断,仙境也就是仙人修炼的场所,道数称之为洞天福地。 二、洞天福地今何在? 明代的文学名著《西游记》第二回描写的菩提祖师斜月三星洞,就是一个典型的洞天福地,书中写道:为求长生之道,石猴千辛万苦跨山越海到达灵台方寸山,只见此山: “千峰排戟,万仞开屏。日映岚光轻锁翠,雨收黛色冷含青。瘦藤缠老树,古渡界幽程,奇花瑞草,修竹乔松。修竹乔松,万载常欺福地;奇花瑞草,四时不谢赛蓬瀛。幽鸟啼声近,源泉响溜清。重重谷壑芝兰绕,处处巉崖苔藓生。起伏峦头龙脉好,必有高人隐姓名。” 无疑,这也是一处风景绝佳的深山幽谷。在樵夫的指引下,猴王来到斜月三星洞,但见: “烟霞散彩,日月摇光。千株老柏,万节修篁。千株老柏,带雨伴空青冉冉;万节修篁,含烟一壑色苍苍。门外奇花布锦,桥边瑶草喷香。石崖突兀青苔润,悬壁高张翠藓长。时闻仙鹤唳,每见凤凰翔。仙鹤唳时,声振九皋霄汉远;凤凰翔时,翎毛五色彩云光。玄猴白鹿随见隐,金狮玉象任行藏。细观灵福地,真个赛天堂。” 在文学家的想象中,仙境除了风景绝佳以外,而且到处都是奇花异草,还有不少吉祥的动物,如仙鹤、凤凰、玄猴、白鹿、金狮、玉象。以现在的观念来看,特别是以道家的观念来看,这才是远离尘嚣的洞天福地,是修行的极好地方。 文学家的想象毕竟是虚构的东西,其实道教的仙境不像佛教的极乐世界、基督的天堂,完全是虚构的,道教的大部分仙境都是实有地方。因为一般来说,道教的仙与神是有区别的,道教的神大部分是虚构的,而道教的仙却是历史上的修道之人。如王乔、王玄甫,魏伯阳、陶弘景、葛洪、钟离权、吕洞宾、王重阳、张紫阳、丘处机等。道教的洞天福地也就是这些得道的真人修行之地。 按照《云笈七签》的记载,道教有十大洞天、三十六小洞天、七十二福地,都是实有的名山。 如十大洞天的所在地:第一王屋山小有清虚洞天,在山西阳城;第二委羽山大有空明洞天,在浙江黄岩;第三西城山太玄总真洞天,在四川崇庆县;第四西玄山三元极真洞天,据说在陕西安康;第五赤城山宝仙九室洞天,在四川灌县;第六天台山上清玉平洞天,在浙江天台;第七罗浮山朱明耀真洞天,在广东增城;第几句曲山金坛华阳洞天,在江苏句容;第九林屋山尤神幽虚洞天,在江苏吴县;第十括苍山成德隐玄洞天,在浙江仙居。 三十六小洞天包全国之名山,如泰山、衡山、华山、恒山、嵩山、峨眉山、庐山、武夷山、九疑山、钟山、天目山等。七十二福地包括更为广泛,几乎遍布全国。 明代的徐霞客,一生游历无数名山。十大洞天中,他就到过第六洞天天台山、第七洞天罗浮山;三十六小洞天中,他到过泰山、华山、恒山、嵩山、庐山。他是实地考察,并且作了详细的记载。下面是他在天台山、武当山的几段文字,读来令人神清气爽。 “入山,峰索水映,木秀石奇,意甚乐之。一溪从东阳来,势甚急,大若曹娥。四顾无筏,负奴背而涉。深过于膝,移渡一涧,几一时。三里,至明岩。明岩为寒山、拾得隐身地,两山回曲,《志》所谓八寸关也。入关,则四周峭壁如城。最后,洞深数丈,广容数百人。洞外,左有两岩,皆在半壁;右有石笋突耸,上齐石壁,相去一线,青松紫蕊,翁苁于上,恰与左岩相对,可称奇绝。出八寸关,复上一岩,亦左向。来时仰望如一隙,及登其上,明敞容数百人。岩中一井。曰仙人井,浅而不可竭。岩外一特石,高数丈,上岐立如两人,僧指为寒山、拾得云。入寺。饭后云阴溃散,新月在天,人在回岩顶上,对之清光溢壁。”(天台山) “共五里,过虎头岩。又三里,抵斜桥。突峰悬崖,屡屡而是,径多循峰隙上。五里,至三天门,过朝天宫,皆石级曲折上跻,两旁以铁柱悬索。由三天门而二天门、一天门,率取径峰坳间,悬级直上。路虽陡峻,而石级既整,栏索钩连,不似华山悬空飞度也。…… “十四日更衣上金顶。瞻叩毕,天宇澄朗,下瞰诸峰,近者鹄峙,远者罗列,诚天真奥区也!遂从三天门之右小径下峡中。此径无级无索,乱峰离立,路穿其间,迥觉幽胜。三里余,抵蜡烛峰右,泉涓涓溢出路旁,下为蜡烛涧。循涧右行三里余,峰随山转,下见平丘中开,为上琼台观。其旁榔梅数株,大皆合抱,花色浮空映山,绚烂岩际。地既幽绝,景复殊异。”(武当山) 徐霞客如实地描写了洞天福地的景色,没有加什么文学的想象,读之使人如身临其境。不过,道教既是一种宗教,而且是以神仙信仰为其归宿,必然要构想设置一个彼岸世界作为现实世界的补充。 道教的神仙本是一种理想,求道的人们希望“登虚蹑景,云裳霓盖;餐朝霞之沆瀣,吸玄黄之醇精;饮则玉醴金浆,食则翠芝朱英,居则瑶堂瑰室,行则逍遥太清。”而这些现实世界是不可能存在的。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、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有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。 虽然这些鸿沟难以跨越,但道教认为,只要虔心修道,功德圆满,人神是能够相通的。明未冯梦龙编的《醒世恒言》第三十八卷“李道人步入云门”,就描写了这样的奇遇。 隋文帝开皇初年,青州城的李清为求仙深入云门,他的子孙将他从山顶的一个洞穴中用绳子吊下去,经过一段黑暗的摸索,当他钻出山洞时,“忽望见树顶露出琉璃瓦盖造的屋脊,金碧闪烁,不知甚么所在?他赶到那里去看,却是血红的观门,周围都是白玉砌就台基座。共有九层,每一层约有一丈多高。” 书中的一首词具体描写了如此的仙境:“朱甍耀日,碧瓦标霞。起百尺琉璃宝殿,甃九层白玉瑶台。隐隐雕梁镌玳瑁,行行绣柱嵌珊瑚。琳宫贝阙,飞檐长接彩云浮;玉宇琼楼,画栋每含苍雾宿。曲曲栏干围玛瑙,深深檐幕挂珍珠。青鸾白鹤双双舞,白鹿丹麟对对游。野外千花开烂漫,林间百鸟转清幽。”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道观,真正是山中人修炼的地方。它的建筑相当的恢弘富丽,如诗如画。不过,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这些并没有什么困难的,它只是一个风景清幽的古建筑罢了。除了门前的台阶比一般的道观高得多外,其它没有什么不同。这样的景象在古人的山水画中也比比皆是,并非超现实的境地。 三、仙境就在灵台方寸间(心灵内) 真正的彼岸世界究竟是否存在呢?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。现代人研究宗教和气功提出了时空维度的概念,认为除了三维的时空(显态世界)以外,还存在四维以至更高维度的时空(隐态世界)。当然这只是猜想,目前尚难定论。 清代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画壁》记载了一个奇异的事,也许能给我们一点启示。 江西人孟龙潭、朱孝廉偶尔进入一座寺庙,朱生因见庙内壁画《散花天女像》而神摇意奇,不觉“身忽飘飘,如驾云雾,已到壁上,见殿阁重重非复人世。一老僧说法座上,偏袒绕视者甚众。朱亦杂立其中,少间,似有人暗牵其裾。回顾,则垂髫儿,单展然竞去。履即从之,过曲栏,入一小舍,朱次且不敢前。女回首,举手中花,遥遥作招状,乃趋之。朱孝廉因心动演出一段情缘,后因震怒天神,被趋回世间,仍日回到画壁前,朱问寺内老僧因缘,老僧答曰:幻由心生。 绕了几个圈子,返回到问题的始点。中国古代人现实的宗教建筑模拟和文学的虚构论述,说的都是一个事情:凡尘不染的仙境是存在的,它仅存在于人的心灵方寸间。(佘志超) (图片来自网络) |